二进制:有关蒋志作品表述的一种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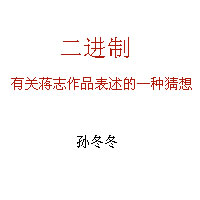
孙冬冬
蒋志的眼前总会出现岔路,这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无法逃脱的现实魔咒。兴奋、分心、恐惧、沮丧,还有不时萌生的警惕,都在驱使蒋志要从嘈杂的中国语境的包围中挣脱出来,好让自己的作品重又遁入到尘世之中。“出”与“入”——这似于围城式的悖论,藏掖着蒋志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机制的某种怀疑,“是”与“否”——历久弥新的二元制,鼓动着蒋志——这一个体,将自己的心智构筑成一种立场,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在价值判断上的另一种参照。只是,由静默、间歇的低吟所凝成的姿态,是否能抵御黄钟大吕般的现实魔咒的冲击?毕竟,尘世的林林总总被绑扎在这现实的磐石之上,看上去是如此的牢固,足以击溃雄心,磨灭耐性。于是,辗转、反复,会与蒋志的警惕相伴:当艺术的权力意志无法与社会现实平起平坐时,他会把“自己”幻化成“生活”,用“生活”去引诱现实,用暧昧的感性转借现实诵出的魔力,让眼前的岔路即兴变为成就“自己”的理由。
尘世始终是模糊的,总在吸引我们去揣测。虽然,“尘归尘,土归土”的训诫言犹在耳,但命定的结局并不能停止身体对于尘世的欲望,扼住思想对于尘世的追问。尘埃落定后的死寂,不会有生活,更不需要艺术,艺术是行进的过程,势必要跟在“生命”的身后,亦步亦趋。莎士比亚说人生如戏,有人刚登场,有人已谢幕。每个人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明明是“看”与“被看”的身份同体,偏又不由自主地回避现实投来的目光,因为“看”,让我们成为主体,让我们占据主动,让我们清楚位置,让我们辨明方向,让我们的视觉“增值”,这是每刻都在发生的一种攫取。纵然,互动的目光可以让主体间达成一种仪式化的扯平,我们仍旧难免在不经意时,遭遇到某种逼迫自己垂下眼帘的无名目光,它在激活自我保护机制的同时,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被考察的对象,一个受监视的客体。“被看”是尘世给予我们最无形的压力与负担,而我们通过“看”,为这种不悦的经验找到自己的替身。
的确,艺术家们会比一般人更敏感于“看”与“被看”之间的逻辑循环,这可以被当成他们在职业方面的一种素养,但它所形成的经验绝非是一套作用视觉的方法论的集合,否则,“艺术”至多是一种语言上的高级游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艺术在不少艺术家的手中还只是一种简单且功利的把戏,他们像是艺术界的“珀尔修斯”,策略化的用作品直接反射现实向芸芸众生投来的目光,而作品背后钢铁一般的创作逻辑期待的是灌注在世俗的坩埚中,想要的是冷却后的那份“坚硬”。然而,与这些“英雄们”相比,蒋志作品显现出的却是“软弱”,他本人并不惮于泄露自己同我们一样——一个生活的当局者,无法做到直面生活。
“软弱”,会让生活具有压力感,但也因为“软弱”,压力感才又变得生动起来,至少在蒋志这儿是如此:他关心时间对于生活的冲刷与侵蚀,在意自己身处其间的蜕变,和推己及人地观察与表述,“软弱”就像一枚楔子早早地被嵌进蒋志现实的生活基石中,不能拔取,只允许偶发的颤动。而每次颤动引发出的表述被逐一纳入仿佛是由“二进制”模式语言编写的程序中,不断地在自我验证,因为他的艺术实践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取决于作品信息必须经过个体以折射的方式释放出来。所以,蒋志并不敌视宏大的叙事背景,而是将其设法带入受到限定的个体语境中加以系统地表述,作品给与观者“暧昧”与“模糊”的诗性印记,正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融合所留下的痕迹。很可能,“痕迹”——蒋志式的表述方式在某一件具体的作品中会成为我们阐释其作品语义的障碍,但这所谓的“障碍”实际上从来都是蒋志作品语义的一部分,有时甚至就是全部。软性的诗语渗入刚性的中国现实的各处缝隙,在激发与调动观者全部经验的同时,也在最大限度的时空维度上为艺术争取到获得意义的权利,从而让艺术尽量处在一种绵延的状态中,如同“生活”本身一般。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天安门”、“领袖”这类中国当代艺术传统的符号元素,也能被蒋志一一点拨成勘查中国现代社会个体以及集体心理变迁的逻辑原点,从而将它们彻底地从媚俗的意识形态表征的空洞语境中解救出来。正如许多人所说,蒋志实在是一个“难以归类”的艺术家,也许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蒋志还有诸如像《白色之上》、《乡愁》、《太初》这样的作品,她们比“彩虹”系列、“强光”系列裹挟了更多的文学气质。但显然这些作品不是蒋志偶然的灵光,依旧属于蒋志式的表述,艺术家只是在作品“文体”上做出更具倾向性的选择。一个人在现实的洪流潜行愈久,就愈想浮上来喘口气,因而这些作品回避了过多复杂信息的附着,在语言上会显得更具直觉性,但这些看似日常话语与人生经验交错的结果却径直指向生命的本质,过程的无常与确定的宿命之间的一次次的拉锯,以及点到即止的姿态,活脱就是一出循规蹈矩的正剧脚本,所有波动的戏剧化情绪全被冷静抑或是无情地框定在时间的架构内,而作品所引申出的“终极平等”,则是先验的主宰人类生活内部一切行动的前提。
虽然,“虚无”只是在意识形态上赋予我们独立与平等的资格,但这对于蒋志来说,却是构建自足艺术世界(可以说是一种虚拟世界)的观念基础。因为这样,有关生活内部的一切元素在语言的表述过程中才可以分化为“0”与“1”,并且“0”与“1”势必需要通过彼此配合才能获得某种总体价值上的认定。所以说,蒋志对于尘世的种种表述,不仅是在立场上,还是在具体的表述行为上,都像是在按照“二进制”的语言逻辑进行的试验。而此刻蒋志的“软弱”也只是照面生活本质时所表现出的“谦卑”,一旦他面对社会现实时,这种美德旋即成为他捍卫艺术权利的武器。当然,以上的讨论或许是“二进制”自身普遍性带给我们的一次有趣的联想,但还是不妨为蒋志的这一展览命名为“二进制”,毕竟,蒋志的实践与整体潮流之间的分野太泾渭分明,两者之间的差异用“0”与“1”来标示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