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你的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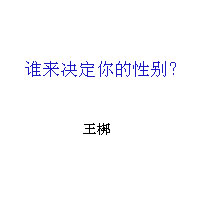
王梆
我很难过整个过程必须如此困难。但若我没走这条路,我又将会是谁?此时我感觉在自己生命的中心,那个梦仍如香甜绿草般缠绕在我的记忆里。
——Leslie Feinberg《《蓝调石墙T》
跨性别运动斗士Leslie Feinberg的小说《蓝调石墙T》,让人回忆起1969年6月27日凌晨那个发生在美国的石墙酒吧事件,为了反抗警方的突袭,同性恋者在石墙酒吧进行了三个夜晚的斗争,此后发展为每年一度的6·27纪念日,并被视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现身Come out)的开端。大半个世纪以来,为性(别)权力的自然化和人权化而斗争的人们——引用瑞典性激进派Lars Ullerstam的叫法则是:“性少数”们,仍在持续战斗。他们中并不完全是同性恋,同性恋只是性少数的一个部分。他们中也包括变性人(Transsexual,对本身性别不满意,而希望透过手术方式改变性别者),反串者(Transvestite,也叫扮异性者,需要穿着异性服装,以女性角色来生活,但不代表希望变性或是同性恋者,大多数的反串者都是异性恋者),反串秀者(Drag),超越了社会对男女性别的生理和心理界定,从本体上到达理想的“雌雄同体”境界的跨性别者(Transgender),以及其他具有多元性需要的主体生命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当代艺术家、DV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蒋志的电影《香平丽》(《Our Love》)正是中国第一部关注“性少数”人群的电影(与《东宫西宫》、《盒子》、《咿呀呀,去哺乳》等同志电影不同)。它以半纪录半剧情片的方式(而非完全的田野调查),向观众呈现了在被称为“奇迹”的深圳,作为性少数的自然物种,快乐、艰辛而无奈的生存景况。影片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为自诩文明和正常的当权者及窥视癖者打开了一道后窗,现身了一座后花园。在这个后花园里,它最大程度地为性少数的妖魔化形象祛了魅。即便是对性少数持“默许”立场的观众,相信在看过此片后,亦会反思所谓的“整体人格病理学”、“心理疾病”、以及现在用于临床的“易性病患者”等包扩来自遗传学的诸多刁难。
我相信在那些被视为异端的电影艺术中,暗藏着人类通往平等和快乐的曲折小径,比如阿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以跨性别者Brandon Jeena1993年的谋杀案改编的《男孩别哭》,蔡明亮的《河流》、贾曼的《蓝》……等等。《香平丽》传达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别政治中的弱势群体发出的声音,倾听它,亦有重要的意义。
一 性阶层中的底层
《香平丽》的主题歌是一首舸非(Ge Fei)创作的《荔枝garden》。它抒情而伤感,像一只逐渐失去燃料的热气球,在摩天大厦中漂浮。在我未到深圳拜访蒋志之前,我并不知道热气球底下那片依稀浮现的蓝灰色绿化带,即是“荔枝garden”。蒋志说,它是男同性恋聚集的场所。这个具有热带狂欢气质的名字,令我想起台北的新公园(后来更名为228和平公园)。在GAY们普遍缺乏GAY BAR的年代,那里曾是男同性恋者的天堂。如同白先勇先生在《孽子》中描述的:“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四处猩猩的狩猎起来。”
然而荔枝garden却不是影片的直接发生地,它只是影片中人物生存环境的一个反射体。与出没于荔枝garden的同性恋者一样,影片中的几位主角是中低收入人群,在性阶层的划分中,他们不属于有经济实力、受人尊敬、有法律保障的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亦不属于符合异性恋道德规范,拥有单一性伴侣的同性恋者,甚至不属于同性恋极端捍卫者所推崇的完全同性恋者,在同性恋圈中,他们被嘲讽地称为娘娘腔的“姊妹”,他们还是“不耻地”使用同性恋性行为的异性恋者。此外,他们汇集所有歧视的焦点——性工作者、高危人群或观赏性性商品。更糟糕的是,他们普遍偏低的受教育程度和世俗经验,使他们害怕沦为最底层,而朝向欺压他们的上层观念靠拢,使他们无法具备激进的“酷儿(Queer)”运动(性左派革命)所需要的理性、勇气和超越力。
所以,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性阶层中的最底层。
他们是渴望做变性人的平儿,反串秀者香香,以及反串秀者丽君。他们在歌舞厅中谋生,他们的受众是同性恋者,观淫癖者和普通观光客,为了赚取多一点的钱(仅仅是多一点的钱)偶尔出台。他们是关系很亲密,同病相连的姐妹,他们全都是不折不扣的异性恋者——把自己视为女性,爱恋着男人。
二 为“妖”祛魅
平儿在影片中以自嘲式的轻松口吻说道:“一日为妖,终身为妖。”
当他们不是河莉秀、金星或者著名的人造变性人美女刘晓晶的时候,社会便把他们叫做“人妖”。这个词总是避不开人们对色情产业的联想,所以即便他们并没有“卖”,亦被当做“卖”的人妖。他们被妖魔化的历史,与突破禁忌的色情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肮脏的性交易”有关。在主流媒体关于人妖的报道中,总是穷凶极恶地突显他们即使做了彻底的变性手术,也找不到合理(法)爱情,只能继续为妖。杨凡的电影《黑街皇后》,即用奢华铺张之笔调表现了妖之佼佼者“人妖皇后”一旦人老珠黄,就被声色淘汰的欲海寂寞。总之,身为“人妖”是一个生命的悲剧。避免成为人妖,就要在幼年时代“坚持正确的性别判断力”。
然而影片中的平儿,却是一个活泼率真,具有某种疯狂的爱的能量的人,而不是“妖”。在舞台上,她敏捷、有力,婀娜而翩跹,丝毫不怠慢她的工作(虽然只是表演钢管舞);在生活中,他爱慕着她的恋人,她希望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彻底变成女人之后,和他结婚。而且他幻想她的恋人先和一个女人结婚,然后生一个孩子,离婚之后再与她在一起,地老天荒。为什么平儿的价值观与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想象基本吻合呢?蒋志认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试图消灭女性性特征,并非是一件好事。他尊重平儿的个人选择,包括“做36的胸,整得像李汶那么漂亮”,以及“想要一个孩子”等等。
难道女为悦已者容就一定会威胁女性的主导地位吗?
接下来,蒋志拍摄了平儿接受塑胸手术的过程。当医生拿出一摞美女照片时,医生的表情是相当愉悦的,这是医生的杰作,在医生轻松诙谐、略显浮夸的描述之中,像“西北首位变性者是位大学生”那种“触目惊心”的新闻效应被不知不觉地瓦解掉了。我觉得这更得益于蒋志独特的影像美学处理——此类略带粗痞的冷幽默:走铁路去香港,电台零点一加一,在胸口上画个圆圈之类,在影片中比比皆是。
影片另一层祛魅,是香香的出场。香香是一个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女人”。她通过略带夸张的、比女人更女人的一颦一笑,不断地确立自己的女性身份。比起平儿,她更接近“雌雄同体”的跨性别者。她的外表,让人想起JAZZ音乐家Billy Tipton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毫无破绽的男人扮相(Billy Tipton甚至还是五个孩子的父亲)。香香希望赚钱,她更渴望爱情。当她被一个叫饶饶的浪漫男人追求时,她享受着:饶饶给她的两条金鱼,一只会说“我爱你”的绒布狗熊,饶饶为她吹奏的口琴,以及深夜里会发光的半导体收音机……然而,现实是——饶饶终于发现了香香她,并不是女人。爱如海边的泥沙流逝。香香又复寂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蒋志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和热情,抒情而伤感地舔着一个女孩在一场恋爱角逐中的鳞伤。
而最关键的是“一个女孩”。
你为什么会在你的影片中特意强调女性特质呢?比如鲜红的内衣、细腻平滑的肌肤、娇嗲的身体语言,甄尼的歌,阁楼上的舞蹈,水、金鱼、绒布玩具?
那是因为,我觉得她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女孩。和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没有女性的生殖特征。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如何界定什么是男,什么是女,仅仅是通过生殖特征吗?——蒋志
之所以观众会为之动容,是因为影片提供了对于香香那样的人物,一个可信度极高的理解平台。这个理解平台则是让被拍摄对象充分地展示自己的美(美丽的身体,美好的情感,对完美的不懈追求)而实现的。是否大多数的人们都赞同:一个有阴茎的人所具有的女性特征,只能以错置和变态来处之的社会,是公平的社会呢?如果当你在视觉上——首先在视觉上,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美”的话。
三 Come out之后的失乐园
丽君是一个男人婆式的“女人”,她是一个从香港到深圳来找生活的歌手,她肥胖,但是她很“明白”,因此“绝对不会去做变性手术”,而且认为“想找一个爱你的人,难罗,找一个你爱的人还差不多。反正爱情就是一场欺骗。”她放弃了对爱情焦虑的等待,转而希冀“大奖中个五百万”。这是她的妥协,也是她长时间以来被社会所歧视而产生的消极心理。她的憧憬既现实而又非现实。
香香以street worker的极端方式,想证明自己的女性魅力,结果却被把她载上车的嫖客狠狠地殴打了一顿——当嫖客发现她不是女儿身时,丽君赶来,背着香香,朝她们的出租屋走去。
影片以平儿在疼痛的煎熬中炫耀自己的芳胸结束:“嘿,比胸大?我回去以后就不穿胸罩,顶死她们!”
饶饶离开了香香,香香被嫖客殴打……虽然蒋志并未着重渲染他们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影片中的人物的服装(全都由演员自己提供)却暴露出他们对现身之后的恐惧。香香和丽君因为女性特征非常明显,所以他们在外出时,总是穿上女孩的衣服,只有在他们的私密空间,出租屋的阁楼和阳台上,才敢于暴露。而平儿的男性特征比较明显,除了演出以外,她在镜头里面总是穿着运动衣和牛仔裤:“我要是做了变性手术,就每天买一套衣服……我喜欢那种很可爱的,显得比较清纯的女孩衣服……”
当人们越来越多的意识到,残障人士之所以成为残障人士,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使更多的可能性,使他们摆脱残障的困扰时,为什么对于毫发无损、心智健全的人,却不能以一种多元化的性(别)视角,正视主体的性差异,看待他们的处境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易性病患者呈逐年上升趋势。据一些专家估算,目前的易性病患者要占我国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左右。当然,这其中有不少是假易性病。让人惊异的是,在真易性病患者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许多还是研究生、大学生及节目主持人。”
——西安晚报的一则新闻
要充分让他(她)认识到手术是不可逆的,把自身的性解剖结构变异成易性结构,从现有性别角色变为易性角色,这是人生所有改变中最激烈的改变,因此,能不作变性手术就尽量不要作,应凑合过去,逐渐顺应性别,改变性格,用各种办法克制自己,自得其乐。
—— 一份关于易性病(transexuals)的治疗方案
公安部门同意手术的证明、包括个人经历及手术决心的个人手术申请的证明、家庭成员同意手术的证明、精神病院排除精神病的证明、工作单位同意手术的证明、乡政府和居委会同意手术的证明、已经结婚者必须解决好配偶问题并出具法院证明、医疗费用的筹备及手术后的生活保障措施证明。所有证明准备齐全后,才能接受变性手术。
一份关于易性病(transexuals)的术前措施
影片中在海中浮现的地雷式的球状体,暗示着现身之后的危险性,即撞击明显是病理化的主流价值观之后有可能遭遇的触礁。我在与蒋志的访谈中获悉,平儿离开深圳回到家乡,男友却与她分手了,虽然分手的原因,未必是因为变性手术。在影片之外,香香也去做了隆胸,然后又迫于家庭的压力不久后取出。血肉的身体——在此,正如蒋志所言,是一个“极限”。一个成为她活下去必须突破的极限。
英美研究学者Jay Prosser引用法国精神分析学者Didier Anzieu有关“表皮自我”(skin ego)说法,将它延伸为体现(embodiment)。他认为:变性揭露了体现(embodiment)如何深刻的构成了主体性的主要基础,但是同时也显示了体现(embodiment)既关乎于肉体本身,也关乎安居于(inhabit)物质肉体时的感觉。
平儿需要一个可以安居的女性的肉体,因此希冀通过事实上存在着风险性的变性手术来实现。在性工作还无法自然化(naturalized)的当下,至少人们应该认同,他的变性是充满对自身关照的,自觉性的表现。但显然,事与愿违。此刻,平儿至少暂时要面对一个Come out之后的失乐园。
福柯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存在的风格,是一种存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而绝对不是一种性身份、性本质或性的种类”。而英国变性人Paul Hewitt 则说“我是为了自己存活所需要的那个身体而战”。
到底,谁来决定你的性别?
塑胸—摘胸,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一样。
看来,这场关于性别的主宰权战争,在影片谢幕之后,仍将漫长地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