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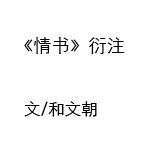
这首诗是悲伤的,因为它想属于你但做不到。
——阿什伯利
“汝一念起,业火炽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
——《水陆法像赞.下八位.一切地狱众》
1
《 》,隔离和区别其内容,诱使我们阅读,却警惕着一泻如注的看,防止或反对,把话语和话语的形式混为一谈。
蒋志的《情书》,因此,并不是蒋志的情书。
后者属于那个独一无二的受信人,此中的私密结构,其爱意、缱绻、哀求、谴责、呼唤,即逸出《 》的部分,以及有待于拥有者处理——回复?认同?置之不理?——才生发的意义,在作为读者或观众的目光中,是绝对的不可见物。
情书是一赤裸的权力关系,没有第三者的容身之处,爱与被爱,告白与倾听,皆不袒露其内情,不为我们所动。惟有《 》保证了某种绝不暴露灵魂但全身心的“爱”再度逸出,超越施受,降临对此无权力的他者。
我们的感受或疑问,也惟有在这一保证下才能以或丰富复杂或简单粗暴——但绝对自我相适——的纹理现身,对《 》中物毫无羞愧或不适的加以覆盖,补加,比拟。
将之放入《 》,就像赤裸者披上随手抓到的衣裳(甚至床单),然后才肯真正出来和冒失的访问者相见。
在此,是可读性在展现,作品在敞露,文本在绽放,不要求知情者身份的物品在与我们协商,寻求对话,吁求联系,容留我们好奇的目光:看哪,这照片,蒋志的《情书》……
2
《 》也意味着,这里的对象——情书——,这个文本,这件作品,这一现成物:它是展示和公开的,可以查阅的,可以翻过来倒过去看的,可以,而且必须放到一个文体的杂多序列里面,检视其位置,尽可能开放其多义性,而不是一上来就封印它:分类,归档,左上角,第一个柜子,第三格……
开放其文本(作品),是主动句,是向文本发起进攻,迫使它门户开放,是假定一个本身开放的文本并不存在,或根本不予承认:一个超验的“临在”永远不可能不经具体到我的经验而下降为真的“在”:必须“做”艺术,必须动手动脚,要用我的已知和未知条件去解除作品的樊篱,要像性致勃勃的触手类一样去侵犯,要不避其猥亵。
无论这里有什么,必经由我们语言的“使用”,并找到一个“趁手”处,才能在语言的手感中动身到场。
蒋志这22张照片,这叫做《情书》者,我(你)要亲自去上手去建筑它所有的视觉性、意义、美感、观念,特别是,必须在此过程中一边干,一边拆除让它赖以如此被讨论的理论脚手架——除非这般目光如炬,意志坚定,否则事情就是: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Rilke 《豹》 冯至 译)
3
但作品后面是有“宇宙”的,必须有。
而且,这有,还不能用它的视觉美和抒情强度加以搪塞。
越是纯净的视觉感受,越是扑面而来的“知道了”,底下越多沉淀、杂质,我脱口而出的“美啊!”越直接和大声,意味着被拦在这声感叹后面的东西就越广大而沉默。
那么,我必须对蒋志作品这不容置疑的美说的,就必然不再是它的“美”了,我应该先试着收回“美”这个词,给它穿系上贞操带,裹上黑衣,让它继续呆在殿堂里面,为它的据传死了的国王——奥修斯(Odysseus)——守丧。
面前这燃烧着的:花朵、树、石头、器皿、地面、台阶、墙体,以及整个这个:这燃烧着或燃烧的物象及其倒映、成像,及呈现——是哪里与如何震惊了我的呢?是一?还是多?是其一定?还是不一定?是作为照片的忠实还是不忠?是事实景象中那发生过的一幕?还是残念般滞留在此的映像?
啊!?是什么呢?
无数次看过和经历过的“燃烧”,去而复来,熄而复燃,一旦在某个中间时刻停下来,就离开,就脱轨,就残骸一般留在那儿——这本身足以让我震惊吗?不,肯定不是。那是我们对照相术的震惊,恒久的,普遍的,令人厌烦的震惊。
然后呢?是不是亚里斯多德般的“悲剧”?美被毁灭在你面前?也不是!——这里无物被毁,没有两个意愿在角力,虽然我投射这一场景内的知性和常识确实提示我,这意味着这件事:花会在这一燃之后迅速枯萎和蔫菸……但那是并不为我们展现也不递交给我们的另一个世界,这绚烂本身,完美无缺地在着,微微灼热,但并无悲剧现身其中。
指针指向下一刻,但永不抵达。——倾向于只差一点点(芝诺(Zeno)意义上),悬置、不停坠落、永恒回归……紧张感一经涌现,就再也不容其退场和衰减,并不停被新的目光加注却永不提供一个满足或决胜的契机。
是的,有物到达艺术家指定的位置,它被强行召唤和控制在此,以这种形式:你被捕了!但罪名?啊,无可奉告……
4
悲剧没有现身。但K的影子,却似乎毫无预兆的出现了……
照片中有一个K,这或是那个一直缠绕着我们言说——通过本雅明、巴特尔、桑塔格——但从未被清楚表述的魅影。似乎智者们就此达成了一致:嗯呐,不清楚的表述更符合K的本质。
但此刻,《情书》里这几样被召唤到庭的物证:花朵,火焰……在烧灼我的舌头,怂恿我去冒险一说,顶替(冒充)它们去说:为什么呢?为何要把我们从自然之梦里惊醒?为什么把我们从自身存在中生生拽出来?为什么将我们汇集到镜头面前?为什么我被我所不知悲哀和忧郁所笼罩?为什么我被召集到你们审视和质疑的目光底下?
不是这样吗?镜头使怡然自得的物,成了进退失据的物象。
这就意味着,再没有不言自明之物了,这儿的一切都在发出这样的吁求:给我一个说法!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YJ)
5
在此,我们提及K或YJ的现身,首先是一种社会学的假性关切,其次在意图一种泛文学化的影像评论,其三其四,声东击西移花接木,使踊跃在键盘字码之间的习惯性话语组合自乱阵脚。
话语在这一行(或下一行)倒下和坍塌,言说就从这一行(或下一行)开始。
6
摄影是囚笼。一定存在一场持续性大规模永不间断地抓捕诱捕和定罪。除非来自艺术家的强制(智慧或痴迷也是一种强制力),世上无物具备类似勇气,下定决心成为一个被截留的物像。
这是艺术家当代工作的核心:堵住,封锁,使尽可能多的对象物无法逃往彼岸世界,甚至使彼岸本身滞留于此在和眼前。
7
蒋志抓住的是“火”。
他用致人酩酊的甲醇诱捕对象物身上的火焰,制造了一幕幕无妄之灾。
这“火”是嗜酒的,肉欲的,成瘾的,狄奥尼索斯般的。它在花粉、花瓣、梗与叶、甚至花瓶的表面啜饮,在树干中吮吸,在巨石的每一道裂隙里舔舐,务实每一滴洒落的甲醇都被火舌吸收。
任何时候,当这一酒神之吻离开,它所触抚与拥抱之物,都将随之而去。
这是物我两造这交相焚映的“业火”时刻,微醺、恍惚、仿佛迷醉,短暂而真实。
短暂?是的,短暂。在蒋志作为作品题语使用在此的一首小诗中是这个词在反复回响——因为惟短暂者真实,长生久视之念,本就是人的虚妄。
以此嗜欲之火,蒋志已将情书焚寄并送达了与之暌隔阴阳者,或作为复信,还递给一个漫长的过去时:无论是此是彼,其中真正的词句、私语、祈愿与谴责、惟施受者所知的小小寓意,在艺术家敞在我们眼前的《情书》中,都只以某种零余存在或倒影般在我们目光的烛照下交错显影。它在我们眼前卷曲着展开,其意指早已脱身,或那是一个“倒着走”,面朝我们,但每一刻,都正在退向更远处。
8
炼金术士们相信,火并非像表面看来一样是一种确切的物质,它更多的是所有雌性物质赖以获得其形式的某种雄性原则。(据加斯东.巴什拉)
爱与死以及目光,或许也一种并不总是具有形式的雌物,她们像先知以利亚一样祈求着火的降临。
但在这里,真正的爱与死已在蒋志寄往某处的情书中被涤除和转化,只有那个顷刻以及被延迟和转移到《情书》里的目光假寐于此。
在这照片中,假寐者半睁着眼睛从净火或业火的道场深处微茫地注视着我们探询的目光。这里无物存在,存在的只是物象。
而这作为物象的《情书》,它凝结和聚拢所有时刻于此在:弃守者与怅望者,离开者与将来者,雌雄同体,在此火浴。
9
“花,一切花朵都是火苗——想要成为光的火苗。”这是巴什拉为诺瓦利斯式的幻想者提纯出的公式。虽然《情书》中的花与火焰,除了无物幸免的喻义式相关,对此公式中的浪漫主义召唤并无更多呼应。
地线、楼梯、桌面、墙角,甚至色彩与款式都极其常见的墙纸等空间因素的存在,实际已经告知我们这里的空间属性并非一个超验构成,花与火焰在这些日常生活空间里具有“事件”特征,尽管依旧有某种“奇遇”或“神迹”色彩,但被这些空间的日常属性对之进行了加注,保证这一奇遇场所属于结构主义范畴,以最小差异原则类属于巴特尔所谓的“抓住现实,然后重组现实”序列。
插花或盆植的器物在构图中的存在是这种结构现实的另一重保证,它们甚至也被延烧和吞噬,成为酒神的欲望对象。
而常见于花店,往来在人际礼仪活动中的这些花朵,其显在商品和消费属性,同样加剧着结构意图的复杂程度……
凡此,不是一声多愁善感的叹惋,一句叹词,甚至一种诗化哲学的所有物。它们在稳定和已经完成的意义世界中没有存身之所,而是从自身的这一属性向另一属性甚至其最为边缘最不真实的可能过渡与转移,逃遁,不停脱身,甚至艺术家本人,也可能因为对最初意图的关切而很快被甩在了身后。
10
《情书》十七至二十二。
从室内到户外,从城市空间到自然郊野,从消费物到自在物,甚至试石以火。蒋志擎火流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的不同的空间对象:这里是失控和着魔的土地,在哪怕最低限度的自然中,人的行为和意图都有可能被模糊或篡改。
我们会想起“自焚”这个词和它的意指。我们还会被“纵火犯”这一巴什拉企图给予解决的心理学形象吸引。
但在所谓自然面前,结构的人最终是乏力的,我们只能倾听其中的文化与情感信息,然后像巴特尔所描述的那样,从反方向感受某种“人类的颤动”。
这是鲁迅式的地火吗?抑或某种炼狱的景观?再或者,这流窜在山石树木上的火焰,它是东方式的物哀与幽明?那种语焉不详并有赖于此不详才能被理解事物和姿态?
11
人是一种审美痴汉,这种迷信一旦被艺术或诗歌激活,一切对其他价值的援引和借用都是不恰当的,不管它是生理学、精神分析、还是任何其他出自布鲁姆所谓“憎恨学派”的知识及其工具,哪怕是一丁点,都构成了绝对的冒犯,足以招致决斗般的回应。
但除非我们进入某些特别的情境或者甘愿在逻各斯链条上一脚踩空,并出于主动去质疑基于对颜色、形状、性状进行一系列联想和拟态,继而建立起来的观感,否则所谓我们的审美将在一切决斗中败北。
“在艺术之中,物质被精神化,介质被去物质化。因此,艺术作品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但是,这些符号是非物质性的,并且,不具有任何不透明的东西。”——如果德勒兹所言不虚,那么我们只有回到各自的目光,这目光不寻找美,是看,看与凝望: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副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寂静——
在心中化为乌有。
(里尔克 《豹》)
12
《情书》,正是此一乌有。
2012年5月18 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