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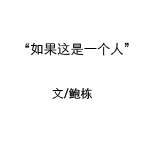
“如果这是一个人”来自犹太作家普里莫·莱维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同名回忆录,开头是一首诗歌,先是这样一段:
| 如果这是一个人 |
安住在温暖屋中的你,
晚上到家有热饭热菜与相迎笑脸的你:
想一想
如果这是一个男人
他在泥水中做工,
他从不知何为安宁,
他为一点碎面包而卖力,
他会因一句“是”或一句“不”而受死。
想一想
如果这是一个女人
没有头发也没有姓名,
没有更多的气力去记忆,
她的眼睛空洞,她的子宫冰冷,
就像冬天里的一只蛤蟆。
⋯⋯
If This Is a Man
You who live safe
In your warm houses,
You who find, returning in the evening,
Hot food and friendly faces:
Consider if this is a man
Who works in the mud,
Who does not know peace,
Who fights for a scrap of bread,
Who dies because of a yes or a no.
Consider if this is a woman
Without hair and without name,
With no more strength to remember,
Her eyes empty and her womb cold
Like a frog in winter.
…
在这段祈祷文格式的诗歌中,作者要求读者去设想一种非人的状态,而如果我们忘记了这种存在的可能,我们将会遭受某种不幸:“否则,你的屋子会倒塌/你会被疾病拖住/你的子孙会背弃你” (Or may your house fall apart,/May illness impede you,/May your children turn their faces from you.)。实际上,普里莫·莱维所强调的可以理解为:如果忘记了“非人”,我们之为“人”的存在就并不完满。
但“人”本身就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完满概念,启蒙思想所设想的人的主体性,是在那根芦苇——即人之为物——的虚无背景上建构的,也就是说,必须设想人之为物的状态,才能去诉求人之为人的理念。而我们或许并不清楚何为人,但我们都知道非人的状况是什么,如阿多诺所言:“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规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我们却非常清楚,什么是非人性的。”[1]在这个意义上,“人”总是意味着人的不在与不是,即非人的在场,甚至“人”只不过是对非人的见证与沉思。这就是普里莫·莱维作为见证者为何反复让我们“想一想”。
不过对于这个展览而言,这“一个人”并不急于上升到那个被作为本体论沉思主题的“人”,反而强调的是某种低视角的经验观察与制度分析,“一个人” 在这里是具体而多向度的,因而总是充满疑问的。这些疑问涉及到艺术家、作品、观众,以及贯穿其间的整个系统。
艺术家是“一个人”吗,这个问题难以明确的回答。一方面,现代主义所建构的那种“个性”概念早已遭到了挑战,如复制、挪用手法的运用以及观念艺术对风格的背弃,这些都已经触及到了对“个性”概念背后的人文主义背景的反思。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艺术实践——作为反思“个性”、“天才”观念的结果,我们越来越不喜欢用“艺术创作”这个词了——不再是某一个艺术家完成的了,以艺术小组、艺术工厂、艺术公司的面貌出现的艺术实践越来越多,他们有的即使依然在强调艺术家的个人色彩,但这已经是把艺术家符号化,乃至广告化之后的局面了。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整个艺术系统——包括生产、传播、消费、研究——对艺术实践的影响力与决定权已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个体。甚至“艺术家”这个概念也面临着被抛弃的境地,因为艺术家与非艺术家之间的区别或许只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处在了这个艺术系统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的艺术家形象,如天才、疯子、高人、英雄、隐士、明星、大人物,可能都会有面对现实情况的不适。于是我们倾向于把具体的艺术家从这些脸谱中还原出来,回到最低的,日常而琐碎的经验中,并暂时把“艺术”搁在一边,只面对这脱魅了的“一个人”的生活世界。
艺术作品呢,它与“一个人”是何种关系。艺术作品中也必然包含着“一个人”,如开头诗歌中的“男人”与“女人”,不过要强调的是,他/她既可能是来自现实,也可能是完全虚构,而他/她又与作者不无联系。当然,与其说艺术家与其作品中的那“一个人”的关系是作者与其影子的关系,还不如说是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而在其中也可延伸出作者与观众的关系。
在今天的文化系统下,作者与观众的关系已经被异化成了一种单向的生产/接受,对于一般的公众而言,美术馆更多地是朝圣与受教育的地方,他们自己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呈现。对应于艺术家的主体性神话,观众总是群体的、无名的,这里有着个人生产与群体接受之间的不对称。
值得提出的是,这一状况的形成与现代艺术系统个展制度的建构有关,时至今日,在大型的国际美术馆举办回顾性的个展依然被视为是艺术家的最终加冕仪式,而每隔一段时间在画廊举办个展也是艺术家职业成长的最基本途径。然而,个展制度是否依然能有效地担负起呈现艺术实践与研究的任务,在目前已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了。实际上,对“个展”概念的讨论,也正是这个展览的潜在主题之一。
正因此,我们在试着去区别于那种约定俗成的“个展”。首先,这个展览无法被归类为回顾展或者阶段性的新作展,实际上,它更接近于艺术史研究性的展览,从一个抽象的议题出发去考察具体的艺术实践,只不过我们把这个议题落实在了蒋志这里。但这个议题——相对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又是生产性的,或许,蒋志过去的工作在我们建构的视角下会被再看一次。
其次,展览主体在这里变得复杂了起来。策展人、美术馆与艺术家之间的互动使展览主体不再仅仅是艺术家个人,而转变成了一个颇为多维的场域。尤其是在这个展览中,蒋志有着多重身份:作为研究客体的艺术家、作为实践主体的艺术家,以及作为策展人。而在这最后一种身份下,蒋志又把“艺术家”的概念与其公众形象作为了他所讨论的话题。但最为有趣的可能是,一位虚构的人物“木木”也加入到了展览主体群之中,而“木木”又可能是任何人,包括任何一位观众。
实际上,在“如果这是一个人”这个主题下有四个展览,策展人策划的蒋志个展,蒋志策划的“白眼人”与“非常地妖的风景”两个个展,以及“木木”的展览,而这些展览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从属关系。
在这种结构下,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已经难以说得清了,既是蒋志这个人,也是蒋志的画家老乡熊望州,或者“非常地妖”这个曾经饱受关注的博客ID,抑或是“木木”这样的木偶与面具? 当然,这“一个人”也可以是与蒋志作品相关的个体,如诗人食指、艺人阿娇,以及蒋志的亲人与朋友;这“一个人”可能出现在一篇文字、一段录音、一段影像、一张照片里,也可能,这“一个人”就在展厅中观看这些作品,或者正在阅读这段文字。
[1] 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 王彤译,谢地坤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