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知作品之后,在事件发生之前—— 表态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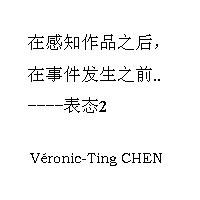
by Véronic-Ting CHEN 维洛尼卡
我在昨天参观了一个摄影展,在许多过道中的一条里,我因为疲劳而放慢了脚步,过道的墙上挂着4幅照片,几乎同样的A2大小,照片里面似乎都是在拍同一个有些年纪但风韵尤存的女人,50多岁。左上一张女人半裸,在整理她的头发,爬满小皱纹的脖子连着松软下垂的乳房,鲜艳的口红,上扬的嘴角指向她慵懒的双眼,眼睛看着镜子,镜子里反射出端着相机的男人,相机挡住了男人的脸。右边过来还是同一个女人,躺在床上抽烟,全裸,“世界的起源”直对着镜头,十分放松,柔软,床的一旁是一个看起来要年轻不少的半裸男人,把玩着一把老吉他,四周烟雾弥漫。下来一张有些不同,要花几秒钟来辩识画面中穿睡衣坐在床角的是上面同一个女人,像伦勃朗的画,四周一片漆黑,而人身上的金色在反射下却尤其耀眼,湿润的眼睛,纽扣,指甲的高光呼应着同样的色泽,周围的空气净洁了许多…我习惯性的把头贴进迷起眼看照片下面的作品信息,短短几个字母:
“我与我母亲”,“我母亲与亨利”,“我母亲在新家中”……
我的心顿时一股纠结……
我停了下来,问自己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之间被感触,然而我却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来描述,没有主题,没有客体。
什么是一个“事件”?
在苍茫混沌之中,一个难以观测的“体”在慢慢外延,一点一滴的,边走边停的,时行时歇的,它有速度,快与慢,运动与间歇,节奏与频率。这个“体”有其“先天”的“截获能力”,使得它在不断外延变化中,获得不同的性质。性质可以被观察:体量,颜色,质感,透明度,折射度,振动频率,膨胀阔值…这个“体”除了拥有“速度”外,还拥有感触与被感触的能力,即其敏感与通感。在这个“体”成为事件之前,它不停的释放其“截获能力”,受到其他“体”的感触,或者去感触其他“体”。
观察者,同样是一个“体”,一个观察者同样有它的外延速度,有它的敏感与通感。一个观察者天生容易被一些性质所“截获”(敏感),在观察者与“体”相遇时,其“主观”开始用于观察,感知甚至表述其所观察的“体”。这就是一个事件。
事件的发生,是体与体之间的相互感触,相互作用。为了进一步去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尝试跟着斯宾诺莎与德勒兹的路线来剖析体与体之间感触的基本元素——“信号”。
首先一个“体”遭遇另一个“体”,并之间相互感触,只有两种结果,即获得能量,成为强大,或者失去能量,成为弱小。这里并没有价值上的好与坏,只有其时间空间性,主观性的直接结果——强大或弱小。
太阳温暖我,“我”在遭遇“太阳”之后,太阳用热能感触了我,使我获得能量,成为强大。这里的“热能”,是太阳释放的信号,这个信号告诉“我”,太阳是热的。同时,太阳光刺瞎我的双眼,“我”失去能量,成为弱小,“耀眼的光”是太阳释放的另一个信号。这里存在的只是一个瞬间性的“加”或者“减”,我们称之为“标量的信号”。然而,还存在另一种信号,感触并不只是简单瞬间的增减,它还可能作用于一段延续的时间,像快感或痛感,快乐与悲伤,都是“过程”,“成为”,“上升或者下降”,我们称之为“矢量的信号”。
德勒兹谈及标量信号一共有四种,第一种是十分基础的性质,来表征“体”的“先天”与“自然”,十分的直观性,物理性与感官性:身为人,我们有体温,有人种,有身高,有重量…。第二种是相对抽象的性质,来表征“体”的敏感,我们只对某些特定的性质会有反应:身为人,我们有理性与情感,我们会笑,我们有植物性与动物性…。第三种是“道德”上的信号,或者“命令性”的信号:因为果实十分苦涩,亚当“以为”他不“应该”去吃,因为太阳发热,我们“以为”它是用来温暖我们…这种信号同时是“因果性”的信号,我们“以为”,感触的结果是“果”,而感触本身是“因”。比如黑人身体适合劳动,白人身体适合思考…。第四种是联想,阐经学或者解义学的联想,先知们的语言,“从一粒沙中看出一个世界,在一棵草里读出一个天国…”把前面三种同时融合起来,表征性的,抽象性的,因果命令性的,阐经术式的…德勒兹称这四种信号分别为:感官的标识,逻辑的图象,道德的象征,形而上的偶像。
同样矢量性的信号有三种:快乐,悲伤与难以言喻(即一种悲伤与快乐共同存在的延时)。
所有信号都有这四个共有的特性:连结性,不稳定性,模棱两可性与类比性。信号与信号间不断合并,分裂,同时作用,环环相连,去构建不同的事件与真实:“解梦者的版本并非都大同小异”,“如何去区分一个成人与一个孩子”,“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死亡仪式”,“我放下行李的地方就是家,我躺下休息的地方就是床”,“我爱得越深,恨得越强烈”……
我们的思考系统,是由100多亿个神经元所组成,每个神经元都有细小的“触手”,连接着其他神经元,一个神经元区域负责处理不同的信号,通过生物电,信号在神经元之中传导着,一个接一个,像打电话一般。事实上,人类思考系统经过不断的思考练习,每个人都搭建其自身的思考系统,即每次有一个信号由感官系统导入思考系统,神经元之间就会开始传导。在精神科学中,有一种临床病征叫分享性精神病:一对夫妻,丈夫是妇科医生,因为之前他们第1个孩子不幸流产,他活在自责的精神压力状态下,他开始出现妄想症,在一次帮妻子进行身体检查时,他检测出妻子怀孕了,欣喜若狂,妻子也十分高兴,对第2胎十分谨慎小心。慢慢的,妻子开始晨吐,浮肿,宫缩,肚子越来越大,在妻子一次外出购物时,顿时感觉不舒服,丈夫在外出差,妻子到医院就诊,这个时候医生才发现原来妻子其实根本没有孩子,是假性怀孕。丈夫的妄想症,某种程度入侵妻子的信号处理系统,他们夫妻之间共同分享着一个“妄想真实”,而这种信号让妻子的身体直接有物理作用,出现怀孕症状。
1978年11月18日,人民圣殿教教主JIM JONES带领918名教徒集体自杀,GUYANA惨案成为911之前最大的非自然灾难,绝大部分教徒都自愿服毒,他们还喂毒给自己的孩子,以及拒绝自杀的其他教徒。JIM与他的教徒同样分享着一个“真实”。
我们自身都有自己固有的思考模式,在我们自身文化中不断经过思考练习,从家庭,到学校,到群体,到党派,到国家,到年龄,到种族,到性别…或多或少,我们都分享着某个“真实”,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某个极为复杂的“信号处理系统”,从“见乌鸦为大凶”,到“财富意味着成功”。
二战之后,我们不仅接受信号的方式变得简单,分享“真实”的方式(也就是说分享“信号处理系统”的方式),同样变得越来越简单。这导致信号本身越来越模糊不清,模棱两可。从性别(我们越来越难判断性别的取向),到对图象的怀疑:“美容杂志-整容杂志”,“NASA(美国航天局)-NEVER GET A STRAIGHT ANSWER”,再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广告上的创意谋杀艺术上的创意”,“宗教党派的市场调查”,“上市企业的我思故我在”…我们在精神分裂。我们已经无法去“认识”,去“认知”,而是要根据这些可疑的信息来做决定,“相信”/“不相信”。
回过头来想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阿娇本身是精神分裂的受害者,因为她身上背负着太多“真实”,而每个“真实”的版本都有着不一样的“信号处理系统”:她是女人,和,某人的女朋友,和,某人的女儿,和,某人的好朋友,和,明星,和,小孩子们的偶像,和,喜欢体验的年轻人,和,性爱录象被公开的受害者,和……她哭,媒体说她扮可怜,她不哭,媒体说她不知廉耻…
我们需要处理信号,来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需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才能来“审判”。十分讽刺。
蒋志的“表态2”,是幽默的,是一种反抗“讽刺”的“幽默”。
每个作品都是一个在外延的“身体”,不断截获可以被观察的“性质”,但是以一种很慢的速度,蒋志的作品不断的释放模糊不清的“信号”。是一个“延时”,在我们感知到作品的存在之后,在我们的意识开始处理信号之前,在信号成为信号之前。
我想这里我没有必要扯进来量子物理的观察者理论来增加幽默感,简而言之,事物在被观察前,呈现出无限多的可能性“妈妈,女儿,女人,女朋友,朋友,偶像,演员……”在观察者出现之后,“多”的交叠态消失,事物成为“一”,成为“客体”,或者成为“主题”。
一个男人的道歉的声音,两个男人赤裸半身,两个性别模糊的身体,一个女人在哭,一群女人“娇羞”,一群人在颤抖……我们在这个“延时”之中,与我们自己本身的“信号处理系统”正面交接。在这个“延时”中,我们成为我们本身信号处理系统的“观察者”。
一个声音,一个男人道歉的声音,是谁在道歉?向谁道歉?为什么道歉?是胡锦涛的声音?是胡锦涛的声音!什么场合下说的?向谁说的?他代表谁而说的?难道是…又或者是…还可能是……需要道歉的实在太多了…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个“延时”,从一个声音到思乡情节,一个“延时”,我们试图在弄清楚事情如何发生…一个“延时”,道歉者与原谅者,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意义,审判本身也已经没有了意义,扮可怜也好,不知廉耻也好,都无法用来形容这个状态下的阿娇,一个正在“成为”的阿娇,一个“多”的交叠的阿娇。
我们所在的当下,是如此的层层机关,步步埋伏,道道惊险,我们反抗着,反抗着他人对我们身体与灵魂的审判…我们反抗着每天都要被困扰的耻辱,我们犯过的错,我们尚未被接受的道歉…我们反抗着资本主义的市场调查,把我们归类,制订一长串战略让我们消费,制订一长串战略让我们赚钱,让我们没时间去爱,没时间去恨…我们反抗着全球化的精神分裂,讲着不是我们想着的话,做着不是我们企图的事情,用“为了生活”当借口,封杀我们所有的逃生路线…
政治让我们相信我们无法照顾自己的生活,牧师让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自行宽恕自己的过错,精神分析师让我们相信我们无法了解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媒体让我们相信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真实……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延时”,在感知之后,在主观之前,不是去醒悟“正在发生什么事”,而是去弄懂“事情如何发生”!
“表态2”,不是“表达态度”,而是“表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