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一种欲望/主体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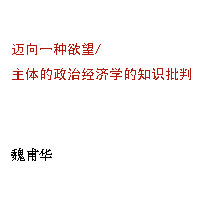
文/魏甫华
巴尔扎克在《老姑娘》(The Old Maid)中写道,现代神话跟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相比,虽然不被人理解,但是更有力量,现代神话的力量源自于它们的想像方式,因为现代神话产于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是无法争辩也无法讨论的实存,它们不是像古代神话起源于奇迹以及人类热情与欲望的传说冲突。当大卫.哈维指出巴尔扎克把巴黎看作是现代性的神话,就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任务。如何理解现代性这个神话,是近代以来各种人文社科思想和现代艺术的思想根源,对这一理论任务的自觉性与否构成了判断知识分子(现代艺术家更多的应该纳入知识分子,而不是狭义的艺术家的范畴)是否丧失批判性能力的知识标准。
福柯晚期在1984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里,好奇地提出:“在中国文化脉络下,是否存在类似狄奥根尼斯的哲学实践者?”这是他在处理犬儒主义和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时惊鸿一逝的电闪火光,却照出中国文人文化与现代艺术之间的隐秘通道。徐冰在《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一文中回忆他们这一代艺术家的思想资源时指出,“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 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所以在纽约,当有人问徐冰:“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可以非常从容地回答他:“你们是波易斯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徐冰还没有触及到毛主义的身后是庄子开创的中国文人文化批判传统。
徐冰强调,“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这就像对待看上去庸俗的美国文化,身负崇高艺术理想的人,必须忍受这种恶俗,穿透它,才能摸到这个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在我看来,蒋志就是这样一位身负崇高艺术理想,穿透恶俗,寻找这个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的狄奥根尼斯式的哲学实践者。
现代社会是由力比多经济学算计的社会。何乏笔在《能量的吸血主义》一文中指出,利奥塔在评论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时,采取了他在《力比多经济学》中所展开的“佛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架构来加以讨论,把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结合起来,即“力比多”(libido)的能量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来探讨“中国古典的性爱论”,并且直接将谈论中国房中术的章节称为“资本”(Le Capital)。和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中,“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一样,利奥塔认为中国房中术中,“精液”所代表的阳气好比是一种“资本”,即“精液”等于某种生命资本,如果使这一资本不断增加,就能达到“能量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只有在强化女人快感的条件下,男人的阳气才能加强,才能形成一种“能量的剩余价值”或“能量的资本化” 。利奥塔进而推论,对于实行房中术的男人而言,主体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性关系属于一种“匿名”(anonymat)的状态:一个男人或许与一千个女人进行性交,但女人对他是匿名的,她只扮演“能量提供者”的角色。然而,利奥塔也提出男女的角色是可以变换的,在“养阳之道”外还有“养阴之道”,所以房中术和“女性主义”问题无关。利奥塔真正要处理的是通过房中术的讨论涉及某种道德关系,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价值等级。因为,在“希腊人对于妻儿从未有这样的观点,而对于冲动的经济学家而言,这正是公民共同体与‘东方式专制’社会彻底被区分的结症所在。”
利奥塔这种中西文化价值等级的论断可以存论,但是他提出的力比多经济学却揭示了全球化下欲望支配经济政治的主权法则,从而开创了一条在全球化下迈向欲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道路。蒋志的系列作品《颤抖》、《谢幕》、《娇羞的,太娇羞的!》以及《0.7%的盐》,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就是对主体为何匿名的勘察,指出欲望通过对主体的宰制获取了对主体的法权。他承袭的就是利奥塔这一欲望/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
黑格尔说,欲望解放了主体,这是现代性出现的一个标志,但他没有意识到,欲望也会吞没主体。主体的消亡,就是后现代性的降临。我们坐在全球化的高速列车上,呼啸而过,很难察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条铁轨相接之间的缝隙可能导致的隐患。我们在后现代消费文化的酒瓶里,也逐渐麻木了神经,丧失了斗志。我们会走向何方,会遭遇什么危险,浑然不觉。这从根本上是我们丧失了理论批判能力,只能在一些知识碎片上构筑我们的未来想象。蒋志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条铁轨对接之间缝隙的探究,从而揭示出两者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解决方案,其关节点在于如何对身体能量(欲望)的资源配置,其背后是全球化资本力量和政治权力的互相碰撞。
蒋志的《谢幕》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思考的继续。这个短片长约 分钟,一个打扮艳丽的女子不停地变化各种姿势,向观众一次又一次地谢幕,让我们想起斯大林的一句经典语录,历史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蒋志在接受访问时指出,权力是不可能自愿退场的。他后一句话隐而未说,那么,革命如何告别?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审查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他对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是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论述主题的逻辑推论,因为革命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法提供过渡到民主宪政的桥梁,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宪政两者之间悬崖峭壁,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深渊。德国魏玛共和之后是希特勒上台,中华民国之后是军阀混战,内乱不止。我们至今仍然走在这两者之间的钢索上,胆战心惊。朱学勤指出,即或是中国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其发动的方式也是采取革命的方式,所以,它本质上不是对革命的终结,而是革命的继续。所以,李泽厚的“告别革命”如何可能?
蒋志的《谢幕》要回答的就是告别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近代启蒙革命最要命的问题是,它是实证正义的结果,不具有自然正当性。如何建立启蒙和自然正当之间的内在关系,需要勘察启蒙的另一条失传的道路。刘小枫在《普罗米修斯之罪》一文中提出了古希腊以来就存在两种启蒙方案,所追问的是为何到了近代以后就只剩下一种启蒙方案了。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被宇宙统治者宙斯治罪,他们之间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而是关涉两种政制理念的斗争,宙斯要的是君主政制,普罗米修斯要的是民主政制,两种政制背后是不同的正义分配原则。宙斯的君主政制建立在神的秩序和人的秩序的等级差异基础之上,是一种等级正义,而普罗米修斯的民主政制要求的是人也要和神一样具有平等分配正义。虽然普罗米修斯也承认神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身体是不死的,而人的身体是会腐朽的,但他不同意宙斯对人类这么苛刻所以他出于怜爱要为人类讨一个说法(怜爱和民主政治相关?法国革命喊出三大政治口号,其中一条就是“博爱”,另外是“自由”和“平等”)。所以,刘小枫说,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思考身体政治的政治哲学家。身体是政治争夺的战场,近代启蒙革命的理由是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主义者也好,新左派也好,现在看起来打的不亦乐乎,其实都是近代启蒙革命的思想产物,最终还是要落到身体感觉上来。现代性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理性,通过知识对身体的规训,但最终却导致理性主体对情感主体的绝对控制,人被关进了理性的铁笼(韦伯语)。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造反革命的第一枪。福柯接着指出人之死,彻底粉碎了启蒙的革命历史,却挖掘出了回归身体感觉的另一条启蒙的道路,这是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的启蒙方案,即自然正当,区别于十七十八世纪以降的实证正义所规定的启蒙方案。
身体感觉就是自然正当?刘小枫指出,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去天火的技艺的同时,也带给了人类盲目的希望。希望是人类欲望的一种,属于人的身体感觉的范畴。正是因为人类盲目的希望构成了革命的原动力。所以,这里的关键是要审查哪些身体感觉属于自然正当,哪些不是?
蒋志在《谢幕》中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舞台占有者不愿意退出舞台的权力表演机制,其实要构成这一表演的完成必须要有被强制的观众,就是说,舞台占有者之所以能够不停地表达自己属于舞台舞台属于她的身体感觉(欲望),是因为观众必须被迫接受她的演出,没有其他选择性,这就是专制权力和民主权力的区别所在。联想一下最近网络流行语“被就业”,就会发现蒋志的狡黠之处,作为观众的我们只要进入他的作品展出场地,就成了谢幕者的“被观众”一员了。
其实,不止作为观众的我们的身体感觉处于被强制的被动语态,表演者自身的身体感觉何尝又不是处于权力机制所控制的被动语态呢?“谢幕”意味着舞台占有者已经不再具有拥有舞台资格的合法性,不停地表达致谢,其实是希望获得“被观众们”的挽留,但她清楚地知道,“被观众们”无法决定她的去留,“被观众们”的掌声与其说是对表演者演技的称颂,还不是说是殡仪馆告别的花圈。谢幕时间的长短已经无法改变权力机制本身,只是表演者个人身体能量差异的展示。这就需要切入到利奥塔的能量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的政治强人一旦谢幕就崩然倒塌,有的却仍然能够不停跑到前台来挥手示意。这样一种权力生产体制,才诞生出中国老子的政治哲学:看谁活的时间更长。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终归未能触及在全球一体化下跨国资本和国家政治力量的双重体制压迫,使得他反而失去了早先提出的“救亡与启蒙”的理论力量,只留下一声叹息。权力合法性来源没有改变,权力机制没有改变,革命如何告别?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历经时间最长,触及社会结构最深,对人性改造最彻底的社会实验。如何理解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我们重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知识前提。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互相糅杂在一起,使得我们的理论重建工作首先遭遇的是语言的困境,传统的话语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话语却仍然在朦胧的地平线摇曳。蒋志对影像的工具选择,或许更多的来源于其对文字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正如汪晖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指出的,“中国的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以至语言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呢?”(汪晖2000)。影像技术的突破,提供了我们一种语言的解放性力量。这一点,蒋志在《娇羞》系列里表现得更加自如。
当然我并不关注蒋志影像技术本身,更看重的是他对这一技术的运用所要表达的思想问题。要重启启蒙的方案,就要回答身体感觉是否自然正当的问题。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核心的思想主题,从20世纪70、80年代对“公共身体”,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受难的身体”,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私人身体”,中国当代艺术的“前卫性”和“身体性”紧密相关。蒋志和很多新锐艺术家对身体“私人性”的注重不同,他从“私人身体”出发,要回答的却是“公共身体”的问题。身体的“私人性”是把私隐作为一种可以售卖的商品,其本质是对庸俗的商品性的投降。蒋志要处理的问题是私人身体如何被公共事件化,要回答的是我们如何逃脱权力和商业资本逻辑的追捕,获得自由尊严的可能。
《娇羞的,太娇羞的!》系列采用了数十个不同年龄阶段(主要是年轻女性)的女性对娇羞感觉的表达。蒋志在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大多年轻的女性们已经全然忘记了娇羞的身体感觉,所以,他需要不停地告诉被拍摄者“不要害羞,尽量表演出娇羞的样子”。舍勒指出,羞感是人最基本的身体感觉之一,“是对我们自身的感受的一种形式,因此属于自身感受的范围。”张任之认为,在舍勒的情感—感觉现象学研究中,羞感作为一种感受行为始终具有意向性特征,价值是它的意向相关项,并且它所指向的总是个体的肯定的自身价值(而与否定的价值无关),而且所指明的总是“将来之物的价值,而不是现存之物的价值”,也就是说,作为“爱的助手”,羞感与爱一样,并非只关注已被给予的现存在手的价值,而是意向一种比现存价值更高的潜在价值或将来价值。羞感始终产生于较高级的意识等级与较低的本能意识的碰撞,在羞感中,我们体验到某种观念的“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冲突,或者说是两类不同层级的价值(更高的将来价值与较低的现存价值)的冲突。国内学者倪梁康和陈少明分别处理了中国文化经验中的“羞恶之心”概念,意图探讨建立和孟子“恻隐之心”具有相等地位的羞恶伦理学的可能性。蒋志的《娇羞》系列无疑提出了建立中国羞恶伦理学一个重要的知识学问题,即如何勘察娇羞这一身体感觉的现象学知识性质。
舍勒区分了羞感两者根本不同的形式或类型,一是身体之羞或生命羞感,一是灵魂之羞或精神羞感,指向的是羞感两者形式背后的价值等级差异。舍勒还区分了羞感的自然表达(因羞而脸红之所谓“羞红”)与羞感的人为表达(如穿衣),这两者都仅是羞感之表达,而不是羞感本身。蒋志的《娇羞》系列处理的是舍勒后者的问题,即对羞感的表达问题。和舍勒区别的是,蒋志的问题是,为什么需要通过阻断害羞,女孩子们才能获得娇羞?和鲍栋在评论时指出,“女人不害羞,男人就会害羞。”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情感阻断性质。舍勒强调羞感是一种意向性情感,这种意向性指向一种自我肯定的价值。而蒋志处理的“娇羞”指向的却是一种自我否定的价值,通过阻隔或者否定自己的羞感价值,从而获得“羞红”的表达效果。这说明我们要处理的娇羞和舍勒的羞感是不一样的,需要我们重新对中国文化经验里的“羞恶之心”进行现象学的审查,否则,建立中国羞恶伦理学的可能道路还会落空。
“娇羞”和身体的自然感觉无关,而是和商业制造有关,这是我们在处理身体感觉是否自然正当必须要认真诊断的问题。《0.7%的盐》是明星阿娇一个从微笑到哭泣过程的表情,选取《0.7%的盐》作为标题,是因为经过科学检测,人的眼泪里含有0.7%的盐。蒋志意欲让自己站在作品之外,尽量让自己的价值少介入作品之中,从而开放更多的解释空间给观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作品选取阿娇本身就隐含了阿娇所具有的新闻性。
这种科学性或许也是蒋志给我们撒出的一张网。阿娇从微笑到哭泣的表情,包括眼泪,其实和我们的身体感觉的自然表达无关,它是人为制造的表达,是明星市场的商业机制逻辑的产物。这一商业机制逻辑和权力机制逻辑一样,同样需要处于这个双重机制被规训的观众的友情出演,我们就在其中。
蒋志的努力是让我们追问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里开启的启蒙新问题,如何理解身体感觉就是自然正当?这首先需要我们对身体感觉进行现象学审查,区别哪些是自然正当,哪些不是。否决现代艺术去政治化的策略性逃跑,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为全球化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准备知识条件。当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在近200年前给理论和行动之间划下了清晰的界限,我们的艺术家们是否继续“为艺术而艺术”的“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语),还是走向街头,走向大众,这是蒋志给我们提出的一个类似哈姆雷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