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谢幕的思考和颤抖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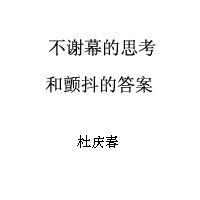
——蒋志《表态》个展的思考
杜庆春
作品对于一个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在一个被命名为“表态”展览中展出,这次展出的副标题是“蒋志的一个展览”。也就是“表态”只是这个人的一个展览,他还有其它的展览。这个展览被命名为“表态”,是不是意味着“表态”是蒋志的作品和作者关联的一个维度、选择或者意涵?蒋志曾经做个这样的表述,“其实我也是套用了一下布罗茨基的说法,他说:‘在写作这门职业中,你积累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疑问,这便是技巧的别称。’”那么,在“表态”展中的作品,蒋志的疑问以及被表现出来的作品之间究竟是何种“表态”?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北京站台中国A空间举办的这次规模不大的展览,其策展人鲍栋在他的《蒋志:在诗学和社会学的交汇处》提及,“蒋志总是自觉地处在诗学与社会学这两个维度的交汇处上,他所着力的是如何使那些我们熟悉的日常、社会经验转换进作品文本中,并保持日常经验与文本经验两个维度的张力。”诗学如果是一个艺术家可以转换为技巧谱系的认知系统,那么社会学的一个巨大的功用在于对于这种谱系产生一个超越这个谱系狭隘语境的质疑,或者将对于自己的技法的质疑这种行为和反思需求工具化。这种将问题、提问工具化的方式本身也具有很强烈的社会学意味,质疑的资源和“现实”的开口都构成了某种社会学的面貌。此刻,一个关键问题来临,如果艺术的表达技巧归结为疑问。那么,这个表述的背后将产生一个广大的讨论空间。回到蒋志这次展览的语境,一个作品是一次表态,这次表态会带出疑问,对于疑问,表述者需要追加解释,所以产生了持续的表态。如果,一个表述者不再为此作出解释,所以在作品中产生了隐晦的空间。隐晦的空间产生了一种艺术的暧昧性——你可以如此理解,但是这种理解肯定是不够的。
蒋志的系列作品的诗学和社会学的交汇是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艺术的暧昧性呢?这种艺术的暧昧性一方面在于解释的不确定性、艺术表述和艺术作品拒绝确定的解释;另一方面在于艺术表达的宣泄性正好要调节是理性之思不能提供完整认知系统,或者说在这种思想的安静来临之前的宣泄才是艺术表达最佳状态,艺术创造的安静是对于滑动的紧张感的捕捉,将其凝固成不动之不安。蒋志的作品能否正好处于这种“焦虑”之焦点上?它们一方面将社会学或者社会性事件带来的冲击安静地放到艺术修辞的位置,逃离其原初的社会文本的具体的意涵,而将这种冲击反馈成一种“反记者报道”式的艺术沉思,但是又在这一列作品中依然保存具象呈现层面上的原始联系。那些形象依然被清晰可见的直接引用了,或者这些被清晰保存的形象的作品成为蒋志作品中最被关注的作品,赞扬最多,抑或质疑最多。
在“表态”展中,《娇羞的,太娇羞的!》和《0.7%的盐》可能直接的构成了上述讨论的印证。芙蓉姐姐和阿娇(钟欣桐)的形象被直接引入,这种引入对于相当多的观看者而言,她们不仅是性别形象而是一个社会文本的沉淀物,不仅是面孔,而且是叙事。在这两个作品中,作品的意涵包含着三个层面的信息:1,女性本身的可凝视性。在这里这是作品最坚固的“内核”,女性本身的可凝视性的色情性和两性权力在这里不仅不能被挑战,而且被强化,被最终巩固。这两个作品所有的因素都可以在“看”的过程中被忽略,比如,艺术史背景知识、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如果,在“看”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色情性被拒绝出场,那么这两个作品在本质上成为“不安全”,那个时刻也许才是最终的反思时刻;2,对于色情的艺术媒介功用。在这个层面上,《娇羞的,太娇羞的!》西式大画框是建构和解构作用同时发生的,在建构对于芙蓉姐姐的形象提升的同时,又解构社会经验中艺术的地位,但是强化了“被凝视性女性”的正当性。在《0.7%的盐》中投影的展示作用,建构了摄影机“看”的权力,摄影机“看”的权力是艺术性的前提,也是意识形态性的,摄影机不仅可以是主观的,而且可以是集体无意识的。而阿娇的新闻事件恰恰都是出现在摄影机“看”的意涵上的,摄影机都代表着社会进行了表态——在这个社会意识中有权利接纳对女性的偷窥,对此行为的指责往往只不过是平衡这种欲望的权力的正当需求。这个展览中,这个作品非常直接的让阿娇再次被看到,当然也包含着“她”再次被拍摄了。3,标题。这两个作品的标题才更为直接地带出了社会学涵义。“娇羞”和“眼泪”(0.7%的盐),娇羞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它的意识形态的尖锐度自然大于“眼泪”依然带有的生理性的中性,当然阿娇的眼泪被道歉这种潜在文本强化了,也变得高度的意识形态性了。
在这两件作品中,蒋志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发问方式以及其等价物“技巧”的状况,在上述关于这两个作品的三个构成元素的讨论中,已经相对清晰地的呈现出来。蒋志的作品直接回应了社会性的冲击,他的艺术创造又采取了一种将社会文本在艺术修辞中隐去的方式,但是不但在作品中保留了社会文本中的“形象”并且更加依赖这种“形象”对于社会文本的附着性,而没有更进一步去将这二者同时置于发问的对象位置。
超越这些已经被命名的“形象”,这次展览中我面对更多无名的形象。在《颤抖》一组裸露的全身人体被投影在不同的幕布上,他们/她们各自占有自己的领地,除去都是颤抖的赤裸的身体之外,他们/她们之间没有相互关联,他们/她们是作为“无关个体的集合”被呈现的,而不是作为“集体”呈现的。因此,“颤抖”如同一个个不同的个案而构成的一个“症候”,观看者对于这些个案可以进行互文研究式的对比,这种对比可以思考蒋志作为作者的采样的思维方式,但是一个“集体”依然缺席,这种状况如同人种学的集体和人类学的一个群体的观察差异。颤抖如何成为一种相互关联着的人的共同行为而被考察?这个作品在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观测,呈现出蒋志对于人类行为、病情的耽溺,一种艺术家的病理学者化的需求,但是在这里“社会学”的思考被过多的悬置了,颤抖的社会事件性质被屏蔽在外部。作为社会网络中的人际问题在这部作品中停步在蒋志的视野之外,他的社会性思考是一个个体人的尊严和一个制度之间的对抗性思考,而并不是一个人际网络的构成和反思,更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一个个体和大他者的对抗性,而非个体间性的他者性。对此,进一步发问也许可以印证某种问题的实质,在《颤抖》中,“集体”的可能性,或者人和人发生关联的可能性究竟在何处诞生?我等待一个瞬间出现,一种心理认同需求出现,这个瞬间是下述文字提供的,Véronic 关于这个作品的感受“我们存在于这样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能够通过刺激让人进入不由自主兴奋状态,人造帕金森,自发,不自然,但却自以为然……”,正如此文字揭示的,只有当观看者成为参与者,当观看者的身体开始“自发,不自然,却自以为然”出现颤抖的时候,一个新的连带关系产生了。《颤抖》在这个意义上,是自我修养的人类学,观看者个体的身体称为真正的介质,作品如同一个强迫性修养的“公案”,观看者的身体即使是幻象性的颤抖是这才“悟”的征兆。除非当展厅灯光熄灭之后,那些各自幕布上的人体可以相互交流的童话出现,这部作品的真正诞生之处在于观看者开始颤抖。
《谢幕》走在了上述所有问题的反面。而我恰恰认为《谢幕》是一次艺术家将问题作为技巧的胜利。在这个看似“独角”表演的纪录中,关于人际性的、社会性以及隐喻性的全面到场,除去它或许艺术修辞变得耐人寻味的大幅度消失,一种艺术的控制、精致趣味、古典性变得相对离场之外,其它意味则饱满登场。《谢幕》的被拍摄者包含着色情性,但是这种色情除去凝视的机制,还有观众席声音的更为复杂的看与被看的互动关系。这位女性在一段叙事中,在其主体身上凝结了更多她作为一个主体消化过的意涵,这里面不仅有姿态的多重状况,也包含着这个主体本身的不可擦除的痕迹,譬如,孔雀舞、藏族等少数民族舞蹈如何沉淀在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身体上,这个女性的身体就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色情想象的躯体了,她的属性让色情摆脱纯粹性欲可能的讨论中,转换为比如带有话语的交流。这种交流,在观众席上作为“形式”提示呈现出来,也恰好将某种过多戏剧性、情节线的叙事排斥在作为展厅录像作品之外。《谢幕》的艺术形式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走到了反面,它成为看起来最拒绝了艺术修辞的原生态纪录。一个真实的剧场和一次伪演出或者伪谢幕被真实的纪录下来,这次纪录和后期混入的人声构成视听文本所有的信息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只是简单的素材的连接。也就是纪录的权力和被纪录的对象之间构成了最为单纯的修辞关系。在这里可以延伸探讨的问题将发生在一个“暧昧”的领域,在日常生活的现实中,“谢幕”可以单独作为节目被录制吗?“谢幕”可以作为表演而生产意义吗?如果,谢幕本身是一个礼节性的环节,它包含着只有必须下台者才能表演谢幕的礼节的前提,那么,蒋志的这个作品非常直接的将日常性经验转换成一种反思。《谢幕》如果说是直接展示了权力表演机制,还不如说更为深入的提示了这不是对一个不愿谢幕者的反讽,而是对整个“谢幕”的礼节性背后的权力机制的反思。“谢幕”直接的隐喻不是权力的表演,而本身就是权力,在这部循环播放录像的我认定的内在叙事的终点这种表演告诉了我们的结论,这个谢幕者被拖走了,一个礼节性的行为,在权力规则规定的时空中,完成整套演出,所有参与演出的人在这个规则性被榨干了所有的价值,然后,只不过是再次循环这个过程。
蒋志的古典趣味,一种审美的意象,这种传统其实依然强烈的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尤其非常有趣的出现在纯粹隐喻性的作品,概念的隐喻和所谓诗意的隐喻。在《长眠》中,在摇曳的幕布上投射的一张燃烧的面孔,以及这次被布置在一段楼梯的起点和终点的名为《肱二头肌主义,在200厘米的高度》的雕塑作品。这些作品的意涵对于观看者而言,或者非常清晰,力量、权力,或者非常模糊,消逝、哀伤。这类作品对于蒋志而言,也许作为创造个体的在问题袭来,骚动不安之后,思考最为透彻和最为安静的时刻的表达。或者此时,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时刻,作品已经成为答案。
2010-10-6
2010-10-9修正